沈从文为什么写边城别用没用的话来糊弄,请认真回答下,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5/03 22:14: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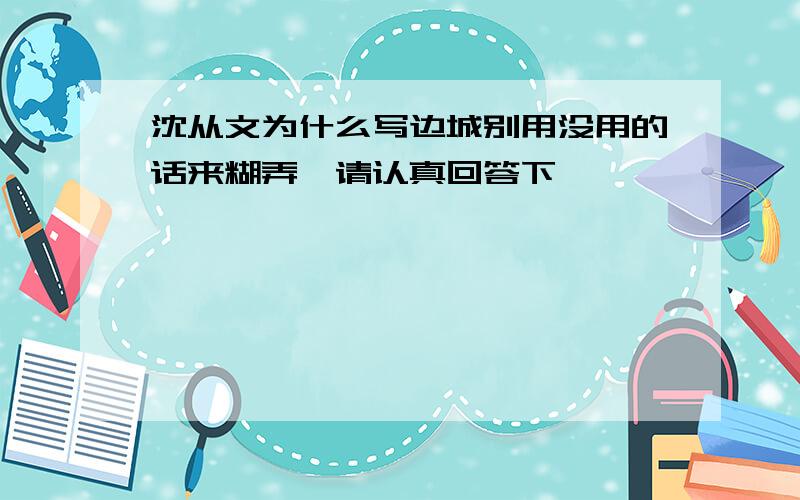
沈从文为什么写边城别用没用的话来糊弄,请认真回答下,
沈从文为什么写边城
别用没用的话来糊弄,请认真回答下,
沈从文为什么写边城别用没用的话来糊弄,请认真回答下,
沈从文创作《边城》的指导思想
沈从文认为社会到处是丑陋,“可是人应当还有个较理想的标准,也能够达到那个标准,至少容许在文学艺术上创造那标准.”(沈《水云》,《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P276—279)——理想
关于《边城》的主旨,沈从文自己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所说的“人性”这个概念与沈从文心目中的苗族文化传统(本质)是同一个范畴.沈从文用“调节异质分布”(rdgulate the distribution of heterogeneous)的方法,首先在话语中构造了湘西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质——这种完全同质(homogeneous)的领域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状态——然后把生活中找到的异质排除到西方那里去,让西方变成自己的“他者”,用“他者”的眼光看出自己的本质(传统).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用以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这就是沈从文的文化相对主义(苗族文化本位)立场,和沈从文全部作品的哲学基础.
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你害怕明天的事实,或者说你厌恶一切事实,因之极力想法贴近过去,有时并且不能不贴近那个抽象的过去,使之成为你稳定生命的碇石”.“那个抽象的过去”指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质,即黑格尔说的“普遍同质的范畴”.“稳定生命的碇石”就是沈从文毕生拱卫的“人性”.
关于《边城》,沈从文说:“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泄与弥补”.这是沈从文通过《边城》寄托他的文化恋母情结的真实的说明,也点出了《边城》故事的悲剧性.
我们可以借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理解《边城》:“……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记录.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
“……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沉痛的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
二、作品分析
(一)《边城》的基调及评论界解读作品的不同视角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也是他的美学思想的集中表现.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作家本人有过重要的表白.他说:这作品所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目的是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作家的表白是切实的.
在小说里,少女翠翠是作家所着力精雕细刻的中心人物.这是作家理想中的“自然之女”,她没有任何都市鄙俗的污染,只有“小兽物”般的天真活泼和“黄麂”般的乖巧善良.而围绕着翠翠所出现的人物,无论是秀拔出群的傩送,还是谦和克制的天保,无论是宽厚仁慈的祖父,还是豁达正直的船总,也都无不保持着做人的美德,信守着灵魂的纯洁.小说正是通过他们相互间的男女之爱、祖孙之亲,父子之情和邻里之睦的描写,生动地层现这边城人民的健康,优美,质朴、自然的人性爱和人情美.
小说无意追求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是着力描绘人物的内心感情.整个作品是那样浑朴天成,如同作家笔下的溪水,顺着山势,或急或缓,自然流淌,毫无人为造作之感.小说的语言也与所表现的内容和谐统一,质朴、清新、自然、含蓄,处处蕴含着浓郁的诗情,字字浸渍着作家的温爱.
《边城》是沈从文长期受压抑的感情的流露.是他自己唱给自己听,为了让自己的心感动起来的“情歌”.
祖父死了,白塔倒了,未成年的翠翠等待着那个不知回不回来的傩送,稚嫩的生命失去了呵护,充满悲哀和隐忧,但沈从文用抒情的暖和色调把人生的悲剧性包裹起来,使之化为淡淡的哀愁,像黄昏落日一样美丽而忧郁.命运难以抵抗,但作品却有一丝暖意:杨马兵――翠翠母亲昔日的情人取代爷爷,负起照顾翠翠的责任;船总顺顺伸出热情的手,而离家出走的二老也还有回来的可能,翠翠的等待并非毫无意义……
一种由沈从文想象中始终追寻的充满人类的爱意的“人生形式”,与人生不可抗拒的命运的悲哀调和起来,构成了《边城》的基调.从这个意义上说,《边城》不是现实乡土的写照,而是作者“排遣”与“弥补”长期受压抑感情的一个桃花源式的好梦.
有人说,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烈的三十年代,《边城》把社会和人心写得这样美,是有意“掩盖现实生活的矛盾”.我们认为,这是对作品和文学社会功能的一种片面理解.其实,美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祖国的山河之美,人民的心灵之美,也是存在的.真实地挖掘出典型环境中固有的真善美,同样是对假恶丑的一种抨击和诅咒.
下面是沈先生写给夫人张兆和的信:
三三,我因为天气太好了一点,故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彻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三三,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我轻轻地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三三,我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的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三三,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三三,倘若我们这时正是两人同在一处,你瞧我眼睛湿到什么样子!
这是一封家书,是“专利读物”,不是宣言,用不着装样子,作假,每一句话都是真诚的,可信的.
从这封信,可以理解沈先生为什么要写《边城》,为什么会写得这样美.因为他爱世界,爱人类.从这里也可以得到对沈从文的全部作品的理解.
历来对于《边城》有这样几种认识:
第一,认为《边城》没有写阶级斗争,“掏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
被认为掏空阶级属性的人物第一是顺顺.有些评论者提高了顺顺的成分,说他是“水上把头”,是“龙头大哥”,是“团总”,恨不能把他划成恶霸地主才好.事实上顺顺只是一个水码头的管事.他有一点财产,财产只有“大小四只船”.他算个什么阶级?他的阶级属性表现在他有向上爬的思想,比如他想和王团总攀亲,不愿意儿子娶一个弄船的孙女,有点嫌贫爱富.但是他毕竟只是个水码头的管事,为人正直公平,德高望重,时常为人排难解纷,这样人很难把他写得穷凶极恶.
至于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向下行船时,多随了自己的船只充伙计,甘苦与人相共,荡桨时选最重的一把,背纤时拉头纤二纤”,更难说他们是“阶级敌人”.
针对这样的批评,沈从文作了挑战性的答复:“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言语上,甚至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
第二,是说《边城》写的是一个世外桃源,脱离现实生活.
《边城》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边城》有没有把现实生活理想化了?这是个非常叫人困惑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小说叫做“边城”?这是个值得想一想的问题.
“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这是个边地的小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这是“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边城题记》).沈先生从乡下跑到大城市,对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对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深恶痛绝,这引发了他的乡愁,使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
便是在湘西,这种古朴的民风也正在消失.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边城》所写的那种生活确实存在过,但到《边城》写作时(1933--1934)已经几乎不复存在.《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
可以说《边城》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
为什么要浪漫主义,为什么要理想化?因为想留驻一点美好的、永恒的东西,让它长在,并且常新,以利于后人.
《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说: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小说的作者与读者》)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这当然为一些急功近利的理论家所不能接受.